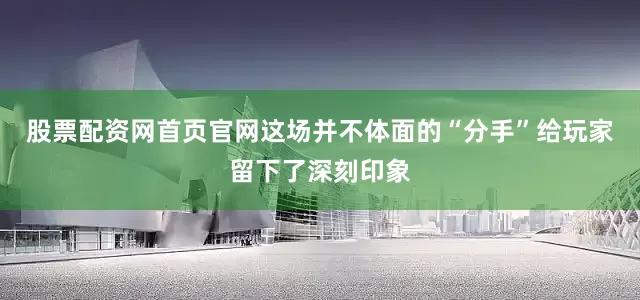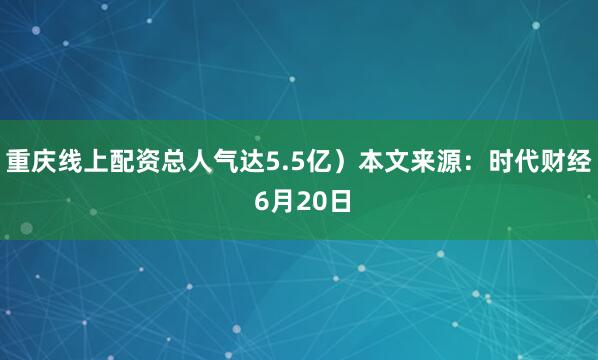5公斤大米4268日元,价格同比暴涨98.4%,创下53年来新高。日本普通家庭开始用电子秤按克分配每日米饭,一场席卷东亚的粮食危机正在这个老牌发达国家蔓延。
“连饭都吃不起了”,东京的低收入家庭主妇们在社交媒体上哭诉。持续飙升的米价已经让大米从日常主食转变为奢侈品。
2025年8月,日本新米上市价格较往年高出约50%,1公斤新米价格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48.8元人民币),一些零售商表示如此高价近年罕见。但这只是开始,市场分析显示,5公斤装大米价格已经突破5000日元大关,且仍在持续上涨。

一、米价飙升,民生承压
2025年5月,日本超市5公斤装大米均价达4285日元(约合215.53元人民币),同比涨幅近98.4%,创下1971年以来最大涨幅。到6月份,这一价格进一步上涨至4223日元(约合人民币209.07元)。
极端高价已经出现,部分高端品种价格被媒体称为“堪比黄金”。普通日本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主食压力,被迫减少米饭摄入频次,部分家庭每周仅食用2-3次米饭。
二、 生活困境,按克称米
面对米价暴涨,日本低收入家庭采取了极端节粮措施。调查显示,约60%的家庭减少或停止购买大米等主食。
有七口之家每日按克级分配米饭:哥哥500克、弟弟350克、奶奶280克,需用电子秤精确称重。这种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常见的景象,如今却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上演。
90%以上的日本低收入家庭难以给孩子购买食物。大阪学校已将学生午餐米饭从每周3次减至2次,有的学校甚至用面包完全替代米饭供应。

三、连锁反应,社会失序
米价飙升引发了系列社会问题。在“稻米之乡”茨城县,2025年前四月发生14起大米失窃案,被盗总量达4.5吨。为应对盗窃,农户不得不将GPS定位器藏入米袋,上演“米粒追凶”。
餐饮行业遭受重创,寿司店、快餐店等面临成本压力,部分商家减少米饭供应量或调整套餐结构。有寿司店甚至需要顾客破解GPS定位才能享用。
受米价飞涨等因素推动,日本4月核心通胀指标加速升至3.5%,给整体经济带来额外压力。
四、气候灾害,供应锐减
极端气候是米价暴涨的直接推手。2023年,日本遭遇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高温和干旱严重干扰水稻生长周期,导致大米产量大幅下降至661万吨,不及历史峰值1425万吨的一半。
2024年情况更加恶化,台风频发,降雨异常,对水稻种植造成毁灭性打击,大米主产区受灾尤为严重。2024年夏季极端高温导致水稻歉收,作况指数骤降至74(平年为100)。
虽然2024年全年产量比2023年增加22万吨,但由于流通体系复杂,集货商和批发商囤积大米,导致市场上流通大米数量减少21万吨,市场供应实际更加紧张。

五、政策失衡,结构缺陷
日本农业政策存在深层次结构性问题。长期实行稻米减耕政策是重要原因之一。二战后,由于大米需求量下降,为维持米价,日本自1970年起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强制减少水稻种植面积,人为控制大米产量。
这一减耕政策直接导致日本大量耕种面积荒废,大米产量逐年减少。数据显示,水稻种植面积从1970年代的300万公顷锐减至2024年的128.2万公顷。
尽管2018年日本宣布废除此政策,但通过“适当生产量”指导指标,政府仍诱导农民转作或休耕,减耕政策的影响仍在延续。
六、农协垄断,操控市场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农协)在本次米价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农协拥有1026万会员,几乎覆盖所有在册农民,控制着全国90%大米的收购、储存和分销渠道。
农协通过控制农业生产、流通和价格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时还涉足于金融、保险、医疗等多个非农行业,拥有巨大的“政治捆绑”能力。由于其同时从事多项非农业务,决策往往以自身经济利益为先,而非考虑农民和消费者利益。
政府为平抑米价投放的81万吨储备米中,95%被农协通过竞标收购,实际流入零售市场的仅7%,导致官方调控完全失效。

七、进口壁垒,自困手脚
日本通过高关税和进口配额严格限制外国大米进入,保护国内农业。对大米进口设置全球最高关税,超出“最低进口配额”(每年77万吨)的部分每公斤征收341日元关税,实际关税率达280%-400%。
这种保护主义政策虽然短期内维护了稻农利益,却导致市场封闭、竞争不足,削弱了农业应对风险的韧性。当日本国内稻米产量因灾害下滑时,缺乏国际市场调剂机制,直接引发供应危机。
尽管国际大米价格在2024年下跌(泰国5%破碎率大米FOB价从年初659美元/吨降至年底523美元/吨),但由于高关税壁垒,日本消费者无法享受到国际市场价格优势。
八、成本攀升,老龄加剧
生产成本持续攀升加剧了危机。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波动和日元贬值,日本进口化肥价格上涨30%,柴油和电力成本增加25%,机械修理费用上涨15%。
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严重。日本稻农平均年龄已达71岁,2015-2020年农业从业者减少25%。肥料、人工成本上涨使水稻种植年收入仅9.7万日元,年轻人不愿务农,农业可持续性堪忧。
九、政府应对,效果不彰
日本政府在危机中反应滞后且效果有限。2024年8月,当日本多地出现米价暴涨甚至“米荒”时,农林水产省以投放储备米恐对市场流通造成影响为由拒绝地方政府投放储备米的呼吁。
直到2025年2月份,米价仍继续大幅上涨时,日本政府才决定向市场投放储备米。但这一政策存在制度缺陷:投放的储备米量少,仅占年需求量的3%。
为了维持储备规模,政府规定需要在未来一年内回购同等数量的大米,投放储备米反过来又可能进一步推高市场价格,形成“政策干预—价格波动”的恶性循环。

十、深层矛盾,改革困境
日本米价暴涨反映出保护主义政策的长期代价。“减反政策”表面保护农民利益,实则通过人为制造短缺维持高价,导致生产效率停滞。分析指出,日本若放开生产限制,理论上可年产1700万吨大米(现为679万吨)。
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存在冲突。TPP等贸易协定要求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但农协强烈反对。2025年3月美国批评日本大米关税达700%,虽经日方修正为280%,但实际壁垒仍使进口米难以冲击本土市场。
粮食自给率存在虚高与结构性风险。日本大米自给率虽达99%,但整体粮食自给率仅38%(按热量计算),种子、化肥高度依赖进口。若国际供应链中断,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
日本政府计划紧急进口大米并扩大储备投放,但受限于农协势力和高关税,效果难以预估。
有日本人开始赴韩国采购低价大米(价格约为日本一半),甚至单次携带20公斤回国。这种跨国采购行为反映出国内市场的失效和国际价格差异的悬殊。
日本“米荒”危机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即使是发达经济体,若固守保护主义、纵容市场垄断、忽视结构性改革,亦难以保障国民最基本的吃饭需求。
洪萨配资-配资中介-山东炒股配资开户-可靠股票配资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